当问到杨丽萍从舞至今,有没有老师对她的舞蹈影响最深时,她总是很快回答:“没有”。
内向的独立舞者
坐在眼前的杨丽萍虽然经常在媒体面前冒出一些睿智的语言,但她说自己不是一个擅长用语言表达自己的人。两年前在正式采访她之前,杨澜说在认识她的二十年里,听她说话不超过二十句。四妹说,“她以前是个挺害羞的人,特别内向。”
1986年第二届全国舞蹈大赛,团里没有选送杨丽萍的作品。28岁的她自己骑着自行车将录像带送到组委会。有媒体说当时的她得知时间已经截止时大哭了一场,杨丽萍否认,“交给他们之后就没管后事,参赛只是想体验一下。”不久,《雀之灵》一举夺得比赛第一名,她在团里的机会慢慢多起来。
“1998年首次收到春晚邀请的时候,她还不太想上。她觉得自己的东西有点曲高和寡。一个人独舞,会冷场。春晚是比较大众化的东西,偏热闹。”四妹说,杨丽萍推了半天,人家还是让她上了,结果出乎意料。
“一时之间,人人趋之若鹜,扒录像带,剖析学习,全国都是孔雀。”高成明说,很多人不明白杨丽萍成功的原因。“她得天独厚,有着与众不同的想象力。更重要的是,她全部的精力、爱好、关注点都在舞蹈,她又远离政治,塑造了一个唯美的形象。唯美既不能被左倾的人利用,也不能被右倾的人利用,她正好处在两方面之间,而这两方都需用美来标榜……种种偶然性都结合在她身上,而她恰恰又是个聪慧的人。”
“她的创作状态太恐怖了,我都吓一跳,没日没夜,也不吃也不睡,常常熬不过她。”
《雀之灵》后她连续创作新的舞蹈,《月光》、《两棵树》、《雨丝》……这些作品均有唯美、自然的特征。同时也牢固树立了杨丽萍独立舞者的形象。
起初人们发现,她几乎不近媒体。妹妹说,她以前都是独舞,比较内向,又受打压,后来突然光线一下全部照到她身上,她适应不了。她过了好一阵子才发现,应该跟大家沟通。
1991年,杨丽萍看到肖全为三毛拍摄的照片,托人找到他,问他愿不愿意为她拍照。“她站在长城上,跟仙女一样。唯一的感觉就是美,一种天赐的美。”那是肖全纪录到杨丽萍的第一个重要时期。
惊世转身
2003年8月8日,筹备了三年的《云南映象》在昆明首演,当看到无数孔雀纷飞的那一幕,台下拿着相机的肖全泪流满面。那一刻他感到杨丽萍的蜕变,“她不再是那个自私的舞者,一种慈悲从她身上散发。在北京,她是一个自我很强大的独立舞者,只有自我修炼到够强大,她才能去引导别人。”
了解杨丽萍的老朋友高成明也被震动了。“《雀之灵》出来,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震动,我觉得对她是水到渠成。《云南映象》让我看出来她独立创作以外对大型舞台的把控能力,轻重缓急、起承转合,把握得非常好。”
四妹说,“她是在拍了几部电影之后,发现电影、舞蹈,都应该是群体的合力。而她自己经验也丰富了,做的东西越来越好,自信了,觉得应该跟大家互动了。”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,杨丽萍回到云南寻根。在田丰民族文化传习馆一住就是几个月。她花一年多时间走遍了全省,采风期间可以十五天不洗澡。用自己的眼光将采来的作品编排出一台原生态歌舞集。
《云南映象》横空出世,其影响远远超出歌舞范围。文化产业发展、文化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和思考至今还在持续。
杨丽萍说,如果换一个人来编《云南映象》,可能会很难。“他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去传承那些东西。我自认为自己有这个品味和眼光来整合,因为我对它们太有感情了。”
肖全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杨丽萍,穿着和周围人就很不一样,“是一种改良后的民族服饰,她一直在关注民族的东西,对云南就特别有感觉,只是没找到很好的切入点。”
《云南映象》筹备前后,杨丽萍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着装变成了清一色民族服饰。她再次用自己的作品引发社会的思考。但她自己很少参与这些论辩。
聊天到中途,她突然兴起,跑进去给我们拿来红酒和酒杯。喝到一半,她说笑,那天谁谁喝醉撞栏杆上了,这种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跟随杨丽萍有十余年的徒弟虾嘎说,从第一天认识她起,就没看过她糊涂的样子,特别清醒。即使喝了酒,也清醒无比,“她就没有休息的时候,就算不跳舞,她也在思考,看书、看电影、看杂志,她什么都看。”
“《云南映象》后,她突飞猛进,像个生活的智者。那么多农村的孩子,有的有过怀疑,她去做思想工作,让他们跟着她,一路走来。”杨丽梅说。
上一页 [1] [2] [3] [4] 下一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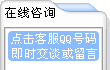


 ENGLISH
ENGLISH 收藏本站
收藏本站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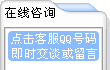


 ENGLISH
ENGLISH 收藏本站
收藏本站